“諸子學”與中華文化複興
發布時間:2022-09-06 作者:方達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自劉歆作《諸子略》後,所謂子學、子部、諸子思想的說法,主要是針對先秦諸子各家各派思想學說而言。而近代以來所謂的“諸子學”,是在中華文化不斷勢弱的過程中,士人針對傳統内部的“經學”“儒學”以及外部的“西學”,提出的一種中華文化新的整體形态。不過,這種“諸子學”本質上隻是針對“經學”“儒學”的弊端,以及“西學”的強勢作出的應激反應,并沒有明确的界定。也正因此,每每提起中華文化複興的議題,“經學”“儒學”便又成為首選。可事實證明,随着中國的現代化與強盛,傳統的“經學”“儒學”顯然已經很難堪此大任。是故,明确近代“諸子學”的産生機理,不失為考察中華文化真正得以複興的牢靠基礎。
從追溯“諸子學”自身複興的曆史角度看,一般都認為自晚明以來中華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交往過程中,“諸子學”先後在明末被視作重振三代政教的階梯,在清末被當作接納西方科學、政治的輔助。而到了五四運動之後,“諸子學”更是被拿來作為颠覆“經學”“儒學”的殺手锏,并期以實現所謂的“民主”與“自由”。不過即便如此,當下學界對“諸子學”之于中華文化複興作用的認識莫衷一是:倡導“經學”“儒學”者秉承陳規,視“諸子學”為細枝末節;研治西學者又将“諸子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一并視為前現代的産物;即便“諸子學”研究從業者,或紮根故紙堆整理國故,或借哲學發明特定理論意涵。究其原因,無不與缺乏對“諸子學”的整體認知相關。實際上,從中華文化内部與從西學關系這兩個角度對“諸子學”進行勘定,不僅是學術工作,更充實了中華文化複興的實質内容,使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得以真正落實。由此,三個問題必須得到解答:“諸子學”在中華文化内部原本是什麼?“諸子學”在中國曆史中如何演變?“諸子學”為何可以消融西學霸權?
“諸子學”原本是什麼
對此問題很難直接給出答案的原因在于,“諸子學”既與“經學”曆史相關,更與“經學”确立機制相關。單純從曆史來看,兩漢“經學”昌盛之後,“諸子學”已經逐漸淪為“器用”之物,原本的整體形态與理論内核不複存在,而這不僅造成所謂的“諸子學”往往在現實中指向某個具體諸子或流派的思想,抑或四部分類中的“子部”之學,更導緻無從直接窺見“諸子學”的原始形态。不過,借助晚明“諸子學”對“經學”形成的批判,與王夫之、黃宗羲等人認為可以由此複歸“六經”之學的這個現象,“諸子學”“六經”“經學”的共同基本特征可以初步揭示。明末批判“經學”,主要目的着眼于革新“經學”在現實制度上的僵化,而僵化的具體表現則是綜合國力的下降。複歸“六經”之學,根本理想在于恢複“三代”政教的活力,得以真正“經世緻用”。而借用“諸子學”,深層原因來自其豐富的教化手段,與對政治體制活力的激發。是故,“六經”之學、“諸子學”以及“經學”的共同特質都是涵蓋了“人倫關系”與“制度設計”。由此直接可見,與唐宋以來将“諸子學”視為“異端”,并僅理解為修身養性之法不同,“諸子學”實際上同樣具有“經學”當中“官師”“政教”的特征。
不僅如此,晚明時人認為可以經由“諸子學”成功複歸“六經”之學,還在無意之中暗示了“官師”“政教”并非如“經學”所示那般,在三代中原本渾然為一,反而是“官師”在某種意義上奠基了“政教”。根據《漢志》所述“六藝”與“諸子”的關系,看似是“諸子”繼承了“六藝”的部分曆史價值與制度理念,并由此自然而然成為“六經之支與流裔”。但綜合考察先秦諸子所論“六經”文獻的意義,以及不同諸子思想對此的發揮,漢代時《六藝略》所說的“五常之道,相須而備”這種統攝能力,實際上反而是經由孔、孟、荀所一脈相承的“仁”“禮”之學所實際創制。換言之,從《六藝略》收錄《春秋》《論語》的實際考量,以及《六藝略》中“大小序”的叙述策略來說,《易》《書》《詩》《禮》《樂》這“五經”實際更多隻是曆史的記述而已,其中所謂的“政教”更多是由《春秋》以及孔門弟子所申發而出。這就說明,漢代“經學”所謂的三代政教合一實際上脫胎于先秦儒家對“人倫教化”的創見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設計,更表明“諸子學”的原本整體特質就是“師教”這種對人倫關系的運思,奠基了“官政”這種具體的政治制度設計。
“諸子學”如何演變
既已明晰“諸子學”原本所包含的“人倫關系”與“制度設計”這兩條主線及相互關系,“諸子學”何時何故變為唐宋時期的樣貌,又還有哪些其他演變的特征,就都顯而易見了。在“經學”的話語系統中,先秦儒家的人倫政治主張成為“諸子學”的價值綱領。對此,漢代今古文兩派以所謂的“周孔之辨”,不斷論證周公、孔子、漢朝在價值理念與制度儀式上的一脈相承,未曾損益。然而,正如事實所示,無論将“政教”的精髓放在周公抑或孔子身上,先秦道家人倫政治主張對于戰國晚期儒家思想的現實影響,以及對秦以來推行集權制度的實際作用,都無法得到完善的處理。由此一來,鑒于“諸子學”與“經學”的原本關系,以及“諸子學”内部“儒”“道”兩家在“師教”觀念上的極大差異,出于維護漢代以後帝國興盛繁榮的實際考慮,後代“經學”的話語必須完全掩蓋“諸子學”原本的理論特征,從而确立自身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也正是這個原因,在漢代“經學”叙事話語中未被完善處理的“諸子學”導緻漢末魏晉時期人倫政治大動蕩之後,終于從南北朝開始逐漸被官方描繪成隻能“入道見志”的個人修為之思。
以此為肇始,“諸子學”自《隋志》開始,不僅在目錄學的意義上以“子部”的名稱,被正式下降到“經部”與“史部”之後,成為三流的思想,而且還通過改變“諸子學”内部流派的排序,徹底模糊了原本的特質。事實上,統治者的這種良苦用心,終于不斷通過曆史事件得到實現。就如唐代雖然号稱“三教合一”,但佛教與道教始終被豢養在“經學”之下。即便短暫在科舉制度中首創“道舉”一科,本質上也是促使道家學說繼續轉向修身養心的道教化,并最終于唐中晚期出現道家思想儒學化的傾向。不過讓人驚異的是,同樣出于維護“經學”在曆史脈絡中的合法性,作為“經學”意識形态的理論來源,先秦儒家也未能逃脫這一擺布,原本以“孝”為本的家國同構,也在宋代理學中被改造成了以“仁”為本的自我道德規約。至此,“諸子學”再也無法真正在“政教”的高度彰顯自身的巨大能量,哪怕經曆了明末短暫的撥雲見日,也最終沉寂在了清代樸學的故紙堆當中。雖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開篇有所謂“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的表面宣揚,但實際上也是以此說明“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家也”的治學當以“經”“史”為本這一原則。
由此,不僅可以将“諸子學”的曆史演變大緻分為漢代經學正式确立前的原初時期、《隋志》之前的“經”“子”争鋒時期、《隋志》至清末的蟄伏期,以及民國以來的義理複歸期,而且同時也證明了“諸子學”可以作為中華文化主體部分的原始身份。然而,“諸子學”僅憑這一身份便可以理所當然複興中華文化嗎?這還關涉“諸子學”之于“西學”的異同。
“諸子學”何以消融西學霸權
正如五四時期以來常常依據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之争的史實,将“諸子學”視作可以迎接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思想資源,甚至通過《莊子》的具體研究發明中華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觀念。魏晉時期的“諸子學”雖然确實體現了對“經學”的沖擊,但深入“諸子學”内部的儒道交互,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諸子流派,“諸子學”顯然沒有也沒必要有西方近代以來所謂的“民主”與“自由”這些觀念。
再次回顧“諸子學”在近代以來的興起,事實上當時中國直接面對的隻是西方基于自然科學的發展而帶來的資本主義發展,五四時期以來對于西方制度與思想的全面學習隻不過是短期之内面對國家與文化迅速衰敗的應激反應。正如“李約瑟難題”所展示的,李約瑟本人首先承認的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與技術領域曾經的先進性,其後才是為中國近代落後尋找思想與制度上的根源。然而,借由庫恩的“範式”理論,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西方近代思想與制度産生現代科學與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反而沒有意識到李約瑟的追問實際上隻是為特定曆史時期的偶然事件尋找一個看似邏輯自洽的根源。由此,學界一邊熟稔“範式”的概念,一邊陷入其中特定的叙述策略而不自知,從而助長了西學的霸權主義。事實上,現實已經證明,即便中華文化與西方近代思想有着本質差異,但并不妨礙中國發展現代科技,并同時在經濟領域取得騰飛。當然,從論證“諸子學”優越性的角度來說,這些成績也可以說在墨子與管子思想中能夠覓得蹤迹。但當西方人自己都已經開始意識到“文化殖民主義”以及“歐洲中心論”的時候,以西方近代成就作為标尺,将中華文化與之比附,還不如平視看待中華文化在接納現代化的同時,有哪些思想特質可以彌補西方思想與制度的缺陷。簡單來說,随着西方民粹主義的日益蔓延,近代西方所标榜的“自由”“理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越發顯示出弊端,而其中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自由”“理性”對于現實世界的逐漸脫離,以及“民主”必然導緻的個人高于群體。反觀“諸子學”中儒、道兩家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二者本質上都強調現實實踐與抽象思辨相結合的重要性,并始終認為“個人”隻是“群體”的組成部分而已。對此,儒家思想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而實際上道家也以“輪扁斫輪”以及“天殺之德”兩則寓言分别給予了明确肯認。
總而言之,中華文化的複興離不開對近代“諸子學”興起緣由的深入反思,而“諸子學”在中華文化中的整體特性與曆史演變,一方面表明無須處處以西方近代價值标準作為圭臬;另一方面更說明不能無視、颠覆儒家思想曾經長期作為中國曆史得以綿延不斷的客觀貢獻。再次從平視中西的角度考量中華文化複興,西方近代以來的發展确有其獨到的先進性,但以“理性”“自由”作為現代科技的必然理論依據,以“民主”作為資本主義的必然制度依據,不過隻是一種特定“範式”而已。中國的複興有自身的獨特性,同樣,中華文化的複興也必須建立在承認自我獨立性的基礎之上。唯此,“諸子學”才能真正在學術層面回歸本原,也才能真正為中華文明複興提供理論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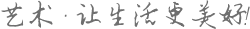





 電話:0531-66570780
電話:0531-66570780 郵件:sdyyjtyxgs@163.com
郵件:sdyyjtyxgs@163.com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黃金時代廣場D座18F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黃金時代廣場D座18F




